
留学苏联期间留影(1962)
张树京,1933年出生于苏州,我国著名的电信工程专家和教育家。1953年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1962年,赴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研究生部深造,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历任北京铁道学院讲师,北方交通大学副教授、教授、电信系副主任、副校长,1983年担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94-2000年,出任上海铁道大学(2000年,同济大学与上海铁道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同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2000年,在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担任资深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为中国的电信工程教育和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北上求学怀壮志
回顾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从求学报国到教书育人,我始终将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视为终身追求的使命。
我是个南方人,5岁就在苏州大儒小学开始上学,当时正值日伪时期,除了要学习日语外,每天上课前,晨歌都要唱日本国歌,1944年,考入了苏州市立草桥中学,1945年抗战争胜利后,学校更名为苏州中学,外语课改为了英语,晨歌改为“青天白日”国歌。我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当时,苏州中学名声显赫,是全国十大知名中学之一。1949年建国后学校成立了党支部,1950年,我以优异成绩毕业,时年17岁,当时想去北方上大学,家人却希望能留在南方,但我对北方有一种新鲜感,同时,通过学校党支部了解到北方因为先行解放,急需大量工程建设人才,于是我报考了东北考区的大连工学院和华北考区的唐山工学院,并先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最终,我选择了历史悠久的唐山工学院,即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后来改名为“中国交通大学唐山铁道学院”,校本部设在北京,我选择的专业是电信工程。
当时唐院的教授很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海归学者。在学习期间,我深受老教授们严谨治学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影响,他们呕心沥血的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才,在我心中,他们的形象非常伟大,我决心向老教授们学习,1953年毕业时选择留校任教。我热爱教育,向往当大学老师,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是平静的,除了教学工作还能利用空余时间通过自学来充实提高自己。1952年,北京铁道学院与唐山铁道学院专业合并,成立新的电信工程系。1955年,我在北京铁道学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
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响应向苏联学习的号召,各地的重点大学纷纷邀请苏联教授来华讲学,我被学校选派到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电信工程系,向莫斯科通信学院派出的专家吉杰列夫教授学习“长途通信”和“信息论”两门课,当时这两门课在国内都是第一次开设。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我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除了听课之外还与其他进修教师在一起研讨专业问题,这期间,我的俄语水平显著提高了。苏联专家的讲课水平很高,内容新颖,有很强的数理基础,并且理论联系实际,让大家领略到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1956年秋季,北京铁道学院聘请了列宁格勒铁道学院派来的专家邱林教授到校讲学,讲授“长途通信”课程,我担任他的课堂口语翻译,进一步增强了我对俄语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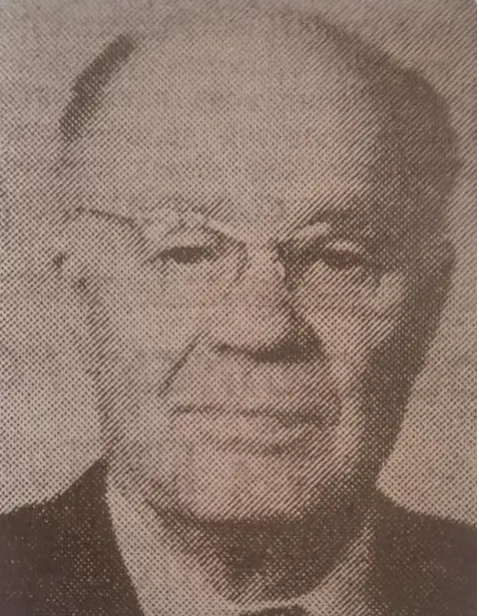
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副教授邱林1957-1958年在北京交通大学执教
经过前两次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经历,我不仅语言能力得到提升,业务水平也有所提高。1958年,我被选派去苏联攻读研究生学位,时年25岁。儿行千里母担忧,家中长辈难免要为我担心,但我知道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放弃会遗憾终身,我再一次说服了父母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同年12月,一列载有上千名中国留苏学生的专列穿越东北松辽平原,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都是优秀的毕业生。他们中大部分经过一年的俄语训练后,前往苏联高校攻读本科学位,只有少数人是去攻读研究生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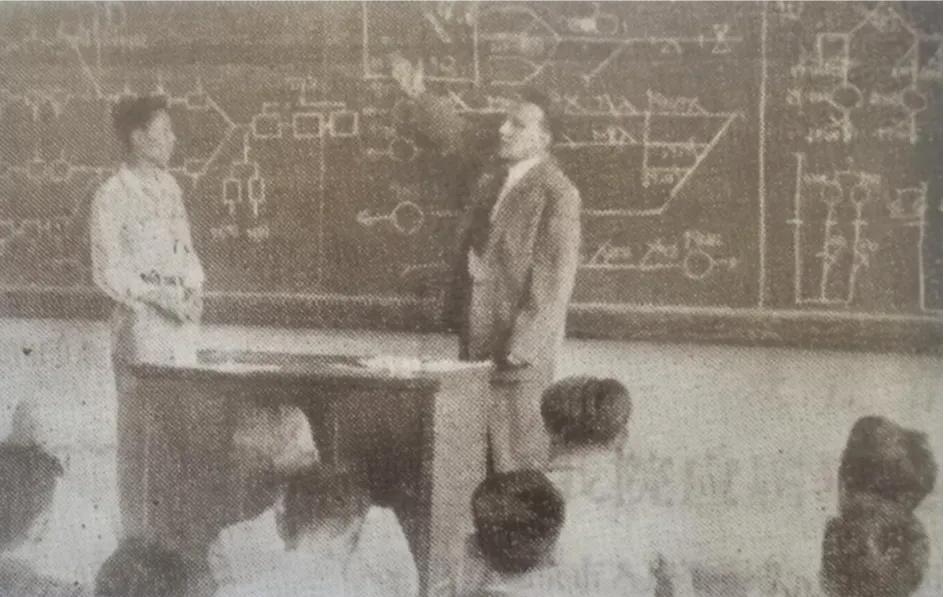
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艾列尔副教授给北京交通大学学生上课
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出国,感觉什么都很新奇,窗外一片雪白,浓密的原始森林不见人影,而在温暖嘈杂的车厢内一切又都仿佛如梦境一般,经过了七天七夜的长途跋涉,列车终于停靠在莫斯科车站。在莫斯科短暂的休整了三天后,同学们开始陆续前往各地的学校报到,我选择了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因为这个学校与北京铁道学院所学的专业相对应,可以更快地适应新的环境。
孜孜不倦求真知
我所就读的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现已改名为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也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这所学校建立于1809年,拥有200多年的悠久历史,曾培养出无数工程技术人才,是苏联铁路建设人才的摇篮。在这里,著名教授云集,包括发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教授,他的实验室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学校增添了不少荣誉。

张树京在导师拉乌拉姆的乡间别墅前留影
在就读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导师拉姆拉乌教授,他是一位德裔苏联人,具有典型的日耳曼性格,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不容许有半点马虎。然而,他在生活中待人却热情诚恳,很容易相处。拉姆拉乌教授在无线电方面颇有专长,他的著作已成为高校教材,并有中文译本,因此在国内早已有名。他指导我的学位论文选题是“微波通信”,这是当时在国际上刚刚起步的全新领域。

在梁赞的第一条微波通信投入使用的铁路上实习
撰写论文工作开始后,我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加紧张。不仅要在校内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还需要专程坐火车去莫斯科的列宁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收集资料,每次回来都带着写满笔记的本子。此外,我还要去莫斯科郊外的“梁赞微波站”实习,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开通微波接力的通信线路,当时是最先进的通信技术之一。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我最终完成了题为《一种新型的微波通信制式》的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了审阅和答辩,1962年获得了苏联教育部颁发的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证书。
在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的四年,我除了享受到黄油面包的美味外,也饱尝了学习的困难和思想的孤独。语言学习是其中的一大挑战,要达到背诵普希金诗篇的水平可谓不易。不仅要应对大量的陌生单词和古怪的句子结构,还要适应不同于普通文章的朗读语调。在与苏联同学一起上课时,语速常常成为困扰,要么全神贯注地听课而无暇记笔记,要么分心记笔记而错过重要内容。因此,每到课后都需花费大量时间复习和补课,才能勉强跟上进度。进入考试阶段后,中国同学们都不得不熬夜备考,很少有人能在午夜前入睡。

然而,在这四年的留学生活,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严格的科学训练,锻炼了独立工作能力。从适应环境到独立生活,从学习语言到写作论文,从交流到答辩,每一步都经历了无数次的挑战和磨练。在成功和失败之间,我体会到了酸甜苦辣,这些经历只有我自己才能深刻理解。然而,正是这些挑战,才让我练就了真正的技能,获得了真正的见识,如今,看到学生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学习,不断钻研问题,我深知这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理解这份艰辛和收获。
肩负重任育英才
1962年的夏季,我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母校。回国后,我被分配到电信工程系无线通信教研室工作。担任“无线电原理”和“无线电接收设备”这两门课程的主讲,其中无线电原理采用的教材正是我导师拉姆拉鸟教授编著的中译本。对于教育事业,我也更加热爱、更加自信了,并立志要为国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同时,我对大学教师的职责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教授不仅需要讲好课,还必须从事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1964年秋季,我曾带领两个班的65届毕业生一起去云南省楚雄市的“铁道兵通信连”实习三个月。主要内容包括架空通信线路的架设和维修,我们真实地体验了部队生活,并与同学们一起接受了军事训练。1965年秋季,我再次带领两个班的66届毕业生去贵阳和昆明铁路工地现场实习三个月。这次实习的主要内容是铁路通信线路的勘察设计工作,大家住在工地,每天要步行十公里以上,晚上还要整理资料。通过这两次“真刀真枪”的毕业实习,同学们不仅增长了许多实际知识,同时也锻炼了坚韧不拔的品格。
1970年,国家为了援助非洲铁路建设,经国务院批准恢复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校名,并开始招收非洲留学生。1972年,全国高校正式复课,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学制为两年,相当于大专水平,接连培养了三届,直到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为止。在这段时间里,除了给无线班学生主讲数字电路和无线电原理课程之外,我还完成了一项名为“船用全波段单边带接收机”的科研课题。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克服了无数次困难挫折,课题终于在1979年通过了该项科研的部级鉴定。该项目被评价为“达到国际上7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获得了交通部重大科技成果奖。
1977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是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并恢复了本科专业四年学制。1978年春季和冬季,各高校在一年内相继招收了两批四年制本科大学生,为学校注入了生机和活力。1979年还恢复了培养研究生和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在当年的第一批评审教师高级职称中,我获得了副教授职称,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1990年,张树京(中)与黄宏嘉院士探讨学科发展
为迎接恢复全国统考后的第一届新生入学,首先要重新编写教材,我主编的教材《通信系统原理》于1981年由中国铁道出版社正式公开发行,后经过几次修订和重印,成为了畅销书,总发行量超过2.5万册,并两度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和优秀教学成果奖励。1978年,经过充分的准备,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我为电信系研究生主讲了“信号检测”和“信息论”两门新课,并指导了两名研究生。从那时起,我将精力放在了研究生教学上,每年招收两名硕士生,论文选题紧密结合当时最先进的科研方向。
1982年,我作为铁道部派出的高级访问学者前往美国进行进修访问,重点任务是学习美国培养博士生的方法和制度,以及学科建设。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学位制度刚刚恢复,尤其是从原来的苏联体制转变为欧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我而言,首先是语言的转变,从俄语到英语的转换需要一定时间,同时,追赶欧美国家的先进水平也是一个挑战。但我对新的目标和任务总是充满了兴奋。俗话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1983年夏,在访美回国前夕,我被任命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从副校长到校长虽仅一字之差,但责任和压力骤增。回顾自己在任校长五年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大概有这样四个方面:
一是主持制定了学校“七五”(85-90)规划。规划中第一次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高等学府,为学校的长远发展确立了目标;规划明确了学校的发展方向,提出要以学科建设作为切入口。二是改变了学校单纯以教学为主的面貌,按照“教学、科研两个中心”,提出着力建设教学和科研两支队伍,并解散基础部,成立物理系,数学系,建立社会科学部。三是进行了分房制度改革,打破以前按平均主义或者按人头分配的制度,提出按贡献分配,调动了教职工的积极性。四是于1984年成立了交大校友会,极大地扩大了学校影响。

1986年7月,张树京校长向全国政协副主席茅以升老校长汇报《北方交通大学1986-1990年事业发展规划》
1984年北方交大的学子受邀参加了国庆35周年大游行。参加大游行的同学们于1984年4月在通州机场完成集结,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集训。七八月的北京室外温度常在40度上下,但是每一次队伍集合,同学们都动作迅速;每一次站立军姿,都纹丝不动。无论教官要求多么严苛,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台前数分钟,幕后数月功。半年的军训磨砺出了军人般顽强的意志与品质。当时大学生第一方队由1万人组成,其中北大5000人,我们交大2500人,北邮2500人。1万人的方队分成2个中队,当天尤其让人们难忘的是,大学生方队行进到金水桥时,在队伍后面突然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我们的大学生方队的同学们也因为这句“小平您好”而永载史册。
1988年夏,我卸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重新回到教学科研岗位。对于工作调动,我心情平静,为能专注于喜欢的工作而感到高兴。从1983年到1988年我的校长任期,适逢中国改革深入,政策法规频出,知识和经验需不断更新,干部年轻化迫在眉睫。个人精力有限,随着年龄增长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希望任期届满后有人接替我的工作,推动各项改革,实现学校的规划目标。在校长任期内,我一直坚持每周讲授研究生课程,每年招收2名研究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所以,恢复教学科研对我来说驾轻就熟,我迅速适应了新环境。

2008年12月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纪念改革开放30年老领导座谈会上
奉献上海开新篇
1989年,我迎来了人生的最后一次大转折:铁道部决定调动我到上海铁道学院任教,以支援师资力量。尽管离开了北方交通大学和许多老同事,但我很高兴能够回到故乡,为家乡做出贡献。1994年,上海铁道学院首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建立了“运输自动化与控制学科”博士点。1995年,学院与上海铁道医学院合并,成立了上海铁道大学,我被任命为信息科学学院首任院长。1994年是上海铁道学院值得庆贺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末,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上海铁道学院获得了“运输自动化与控制”学科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铁路高校中又一个新的博士学位点。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成功申报,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博士授予权和博士学位点,使得学校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上海铁道学院的校史上划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5年,张树京(右)指导学生上机
自1986年开始,我在北方交通大学每年都招收博士生,并成功指导多位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因此,我对培养博士生的全过程非常了解,也明白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我担任博士点负责人期间,一切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1995年春季,我们就成功招收了第一批博士生,其中大部分是青年教师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博士生的入学使学校焕发了新的活力,学生报考博士生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1990年,张树京(左三)与来访的黄宏嘉院士等合影
在上海工作12年的时间里,我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学科建设方面,但与在北京工作时的角色不同。在北方交通大学,我负责学科建设的宏观调控,而在上海铁道大学,我则深入到一个学科中,从培养青年教师和博士生、重点实验室建设,到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等具体工作抓起,直到一批批博士生毕业,项目完成,论文发表为止。这些成果反映了学科建设的建立和完善过程。

学科负责人张树京(右二)与系主任徐金祥(右三)接待铁道部部长韩杼滨一行参观通信信号实验室
我统计了一下,在上海工作期间,共完成了省部级项目8个,新开设研究生课程4门,修订本科生教材2本,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20篇。这些成果是我来上海后的重要成绩,也算是对家乡的一点贡献。同时,国家和政府也给予了我不少荣誉和奖励,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励5项,政府特殊津贴、铁道部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导师等荣誉。这些荣誉和奖励都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内心充满感激,但也感到受之有愧。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尽一个教师应尽的职责而已。

1994年,张树京(左三)在其博士答辩会上
从1986年算起,我在北方交通大学共招收了7名博士生,在上海铁道大学又招收了8名博士生,他们都按期毕业,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此外,我在两校指导过的硕士生共有34名,他们目前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业务骨干作用。2000年,根据上海市教委的批准,上海铁道大学整体并入了同济大学。原来上海铁道大学的通信信息专业并入了新成立的交通信息工程系,同时成立了交通运输工程学院。2001年,同济大学评审了100名资深教授,我有幸获得了同济大学资深教授的称号。我在2002年1月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自1953年留校工作算起,我的教龄达到了48年。
后记
回顾我的人生道路,上世纪50年代是我学习成长的高峰期,从小学入学到研究生毕业,学业都很顺利。而上世纪80年代则是我工作事业的顶峰,不仅在教学工作上认真负责地培养了一批人才,也在行政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责,在北方交通大学的改革开放中迈出了良好的第一步。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依靠自己走出来的。在人生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困难或挫折,但一定要有克服困难的自信和决心,坚持到最后就能获得胜利。同时,也会碰到不少机遇,要牢牢抓住,不轻易放弃。面对工作或学习中的失败,不要气馁;而在取得成功时,也不要过于乐观和骄傲。为人要谦虚谨慎,待人要善意真诚,严于律己,乐于助人。这是我一辈子的心得。
在《我的人生感悟》一文中,我曾写道:回顾我的整个工作事业生涯,可以用“学、教、写、办、情”这五个字来概括。所谓“学”,是指“学而不厌”;“教”,是指“教书育人”;“写”,是指“编著教材”;“办”,则是指“办事认真”;“情”,则是指师生情谊。总的来说,我的一生是平安幸福的。
我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亲朋好友,感谢培养我和成就我的母校,也感谢支持和陪伴我的亲人!

退休后的张树京
刘纲、王苑|作者
张树京、张雷、欧冬秀 等|图片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来源